【識港網訊】「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我其實是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這是瞿秋白在獄中寫下的《多餘的話》。文人與革命,究竟有何糾結?秋白的一生,似乎作了一個最好的詮釋。

秋白出身於常州城裏出了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歷代多為進士舉人,布政使、知縣、五品官鋪滿了瞿氏族譜。然而,傳到秋白父親一輩,開始家道中落。命運的陰差陽錯,讓他走上了政治家道路。1920年,秋白以北京《晨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去俄國,此行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從一個憤世嫉俗、追求個人絕對自由的安那其主義者,轉向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者。新成立的中共當中,懂俄語的很少,而秋白精通俄語,有很深的理論修養,又見過列寧、托洛斯基,他在黨內地位迅速上升。兩年以後他回到國內,成為中共的核心領袖之一,鮑羅廷出任國民黨的高級顧問之後,秋白又是他的俄語翻譯,比其他的中共領袖距離共產國際高層更為接近,當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便指定瞿秋白代替陳獨秀出任中共最高領袖。
秋白是一個好老師、好作家、好的理論鬥士。他激進,有文人般的血氣和衝動。政治鬥爭需要持久的耐力和審時度勢的計謀,但秋白所缺的正是這些。

政治是一個權力場,政治家通常都有強烈的權力欲望與衝動,一旦進入權力的角逐,秋白的文人性格就顯現出短拙,他的權力欲很弱,對控制場面與他人沒有什麼興趣。而且作為政治家要有曹操的「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的狠勁,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以秉承天命的絕對意志粉碎一切擋道的敵人。但文人氣十足的秋白身上多的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鋼鐵般意志,而是從小形成的慈悲、猶豫與寡斷。他在《多餘的話》中承認自己是最怯懦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也不敢的。
據茅盾晚年回憶,在30年代秋白有一次給魯迅和茅盾寫了一封短信,署名「犬耕」,魯迅和茅盾都不解其意,秋白解釋說:「我搞政治,就好比讓犬耕田,力不勝任。我可以做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可以做個中央委員,但要我擔任黨的總書記,就是讓犬耕田了!」作為文人的秋白過於清高,愛惜羽毛,他狠不下心弄皺自己的長衫,搞髒自己的手。薩特有一出名劇叫《骯髒的手》,布爾什維克領袖賀德雷對總是懷疑手段是否道德的文人革命者雨果大聲宣佈:「要成就偉大的事業,就不要在乎你有一雙骯髒的手!」俠客政治家可以蔑視道德,但文人政治家不行,他們有道德潔癖,過於心慈手軟。做浪漫的革命文章在行,從事冷酷的政治行動縮手縮腳,就像布哈林批評秋白那樣,像個娘兒們!

不過,命運終究成就了他,讓這位「多餘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寫下了「多餘的話」——一部中國文學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獨特的經典。秋白被捕後,身為中共高級領袖,並非沒有生的機會。南京方面專門派員赴長汀勸降,許諾只要秋白自首認罪,出去以後可以到大學當教授,化名做編譯工作。並舉先前叛變的顧順章為例,對秋白說:「你看他殺人如麻,轉變之後,黨國還是很優待他的嘛!」看似柔弱的文人秋白,一涉及到自己的信仰、名譽與氣節,立即變得異常剛強、毫不含糊:「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作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作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士可殺而不可辱。沒有什麼比放弃自己的信仰更可耻的了。五四時期的秋白曾說過:「我們對社會雖無責任可言,對我們自己心靈的要求,是負絕對的責任的」。作為一個「多餘的人」,雖然行動的時候一再猶豫,但對於自己的信仰是絕對忠誠的;心靈的自我,就是真實的自我,倘若背叛了信仰,如同行屍走肉。肉體的死亡算什麼呢,靈魂才是永恆的。監獄中的秋白在送給軍醫的照片背後,寫下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

都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但秋白早已視死如歸,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與早年的佛教生死觀,在他內心融為一體。他相信,一己肉身之寂滅,不足掛慮,精神所獻身的神聖事業,自有傳人:「斬斷塵緣盡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欲知治國平天下,原有英雄大聖人」,他可以死而瞑目,坦然西歸了。
1935年6月18日,執行死刑命令的特務連連長走進囚牢,秋白正伏案書寫人生中最後的詩句:「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見劊子手進門,他要他們等等,從容完成最後的跋語:「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

出得牢房,進了戒備森嚴的中山公園,涼亭之下,秋白面帶微笑,神態自若地留下最後的照片。餐畢,信步走向刑場。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用俄語、國語吟唱《國際歌》、《紅軍歌》,四十分鐘的步程,若歸家之路,自如從容。抵達刑場,秋白見是一片草地,鬱鬱葱葱,周圍綠蔭懷抱,鳥兒在吱吱鳴叫。秋白盤腿坐下,對劊子手宛然一笑:此地很好!
槍聲響了,秋白的肉身若一片秋葉,悠然飄下,回歸自然。而他的靈魂,如同火中鳳凰,涅槃永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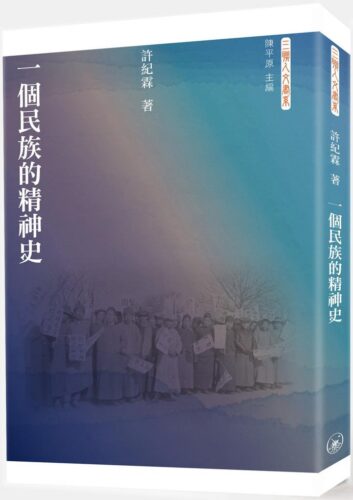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
作者:許紀霖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橙新闻:https://www.orangenews.hk/culture/137634.jhtml



























